巴塞羅那,1962 年。 一場簡單的比賽,進入並弄髒。 剛剛啟動的保險櫃,幾乎沒有監視,更不用說抵抗了。 會出什麼問題? 好吧,絕對是一切。 因此,本來應該是簡單的搶劫變成了殘酷而拙劣的謀殺。 經理 Francesc Rovirosa 在阿拉貢街的燈飾店裡被刺傷,頭部被砸碎。 正如當時所說,這是“存在主義者的罪行”。 十年之罪。 除了所謂的存在主義者實際上是一名美軍逃兵、點燈人的情人、一名攝影師和一名爵士樂手。 一個非典型的“幫派”,以幾乎是新生的 Jamboree 房間作為其行動基地,還有一個開放式酒吧,出售 centramines、酒精和海洛因。
在一個仍被獨裁政權籠罩的棕灰色城市裡,揮舞著毒品和無賴。 “這是巴塞羅那奧運會前的故事,這是我最痴迷的故事之一,”阿爾貝托·瓦萊 (1977) 現在解釋道,他將羅維羅薩的謀殺案及其令人震驚的環境帶回來,並在《每個人》的書頁中將其小說化左起舞'(搖滾出版社)。 “這是一個結合了我所熱衷的三件事的故事:音樂、巴塞羅那和真正的犯罪,”《我是死者的複仇》一書的作者瓦萊解釋說,他還簽署了一個“低俗”系列筆名 Pascual. Ulpiano。
第六艦隊
最新的 L'H Confidencial 黑人小說獎獲得者,“每個人都停止跳舞”在巴塞羅那講述了一個激情低落、資金更少的故事,在巴塞羅那,爵士樂開始作為一種不同尋常的自由堡壘脫穎而出。 那是 Jack's 俱樂部、Toast 和第六艦隊海軍陸戰隊在 Plaça Reial 和 Calle Escudellers 周圍漫遊的日子。 Jubilee Jazz Club,當然還有 Jamboree,它誕生於 1960 年,當時政府的報刊對此感到恐懼。 “事情就是在未經無能當局許可的情況下發生的; 引人入勝、有趣、危險和令人興奮的事情”,Valle 辯護道。

Tete Montoliu,在 Jubilee Jazz Club ABC
這位作家補充說,六十年代的巴塞羅那是“一座處於其自身時代極限的城市”。 “一個落後國家的省會城市,距離歐洲起點和那裡的情況真的非常不同,”他解釋道。 簡而言之,這座城市的貧困足跡仍然很深,苦難遍布小巷和養老院。 “物質苦難導致道德苦難,”瓦萊說。
沒有什麼比一部優秀的黑人小說更有效地捕捉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間的過渡了。 “我認為探索道德苦難是犯罪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非常不同的角度進行檢查”,一位被公認為犯罪小說狂熱消費者的作者指出。 “當時的巴塞羅那是西班牙黑色電影和犯罪電影的首都。 在這裡,他們被拍攝和拍攝,我不會說全部,但絕大多數這種類型的電影。 我一直堅稱,巴塞羅那真正的第一所電影學校是伊格納西奧·伊基諾 (Ignacio Iquino) 和他的公司”,他解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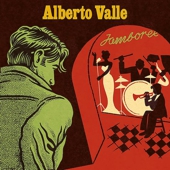
“它是探索道德苦難的黑人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 檢查非常不同的角度»
大量記錄,“每個人都停止跳舞”改變了自己的一些,並引入了一個與勒索和犯罪集團有關的虛構情節,但它也為 Tete Montoliu 和 Gloria Stewart 等真實人物發聲,並捕捉了一個時代的精神因為相對容易絆倒。 “在那樣的時間去黑暗面相對容易,”他滑道。
正是在這裡,皮拉爾·阿爾法羅、斯蒂芬·約翰斯頓、傑克·漢德和詹姆斯·瓦格納即興創作了死亡四重奏,這些死亡四重奏飛越了一個看似完美的群體,但他們卻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據你所知,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對讓-保羅·薩特的作品感到安全,但他們笨拙的冒險讓佛朗哥政權把他們作為一切壞事的例子,他們說,在爵士樂俱樂部裡可能是骯髒的.
